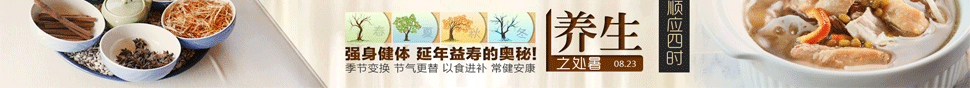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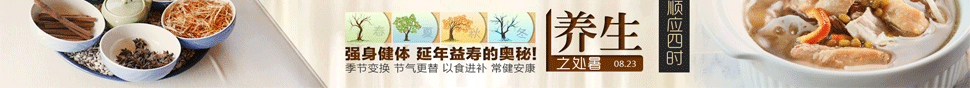
作者创办的中南屋
中美君说:FT中文网与亚洲协会壮志计划项目组联手推出专栏“我所经历的一段有意义的教育”,集结具备海内外多元背景的撰稿人。他们将通过个人故事探讨教育的本质、教育对于个体的重塑,以及教育对于社会精神风貌的折射。教育不囿于校园,它浸入坊间、市井、田野、途中,和人际之间;教育重塑个体,创造自我探索的可能性,同时折射社会的精神风貌。
第一篇,来自中南屋的创始人,黄泓翔。
作者:黄泓翔
编辑:刘皓琳、杨楚
年的尾巴,我的内心是十分焦虑而惶恐的。
像许多人一样,在本科阶段我做了大量的社会实践、实习、研究课题,表面看上去光鲜,实质上却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东西,找不到能闪光的位置,更找不到应该前进的方向。
那个时候,我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发展专业读研究生,就像许多本科毕业了却仍然彷徨的人一样,用读书为自己争取探索的空间。
如果说本科时候觉得自己还是出色的,到了哥大之后,面对这里的老师和同学,我迅速低到了尘埃里。
杰尼克·雷登教授便是这样一个人。他家是一栋并不算特别大特别奢华的房子,然而进去之后走廊两边都挂着照片:在非洲某地的探险,在东非小国刚独立的立法大会,在老上海的奇遇。教授随手从旁边拿起一个木头手杖,开始讲这是非洲多哥的古老兵器,以及这种兵器为什么打不过邻国。
我逐渐了解到,年轻时的他已经通过法律工作游历过世界,帮东非刚独立的国家完成了立法,帮非洲小国与国际石油巨头打过官司。
“我希望我到您这个年龄时,也有您这样精彩的经历。”我对他说。他对着我微笑,眼神狡黠而充满引诱,仿佛在说:世界就在那里,你去啊。
布莱恩则是同学里的代表。三十岁出头的加拿大青年,永远带着腼腆的微笑,然而在课堂与聚会上说起自己的理想从来不含糊:“我希望终结世界的贫穷。”在他生日的时候,他跟大家说,不要花钱买生日礼物或者吃喝,而是用这个预算买一本《贫穷的终结》,送给身边的人。
这些事情,让他在我们同学中极为引人注目。在他看来,你只需要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,并且把它做到极致就可以了。
另一位教授霍华德·法兰其的一句话,大概可以概括我在这里的惊叹。
那天,他带着满脸皱纹与笑容对我们说:“如果用经历来衡量人生,我的人生极其富有。”那一刻,我和我身边的青年同学们,都是充满艳羡的。甚至和我本科阶段实习过的单位的许多前辈相比,他都并非算经济上富有的,但是,本科阶段的实习期间,我从来没有羡慕过任何一位前辈,更没有想过希望成为其中的任何一员。
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部分同学毕业合影
我在哥大的外国同学平均年龄30岁左右,大多是工作过一段时间再来读书。他们的工作经历闪闪发光:麦肯锡、华尔街律所、国际NGO、总统办公室。他们的国际经历让我惊叹:非洲、拉丁美洲、东南亚小国、太平洋小岛。他们知道自己的人生激情在哪里,勇于寻找一种有意思且有意义的人生。
像许多哥大的中国学生一样,我们知道机会来自于社交,然而,这种networking(交际)在优秀程度不对等的情况下,其实是很困难的。
我记得无数次,课后和同学们一起去寻找老师聊天,然而老师的注意力很快被某个同学的某个课题吸引过去;与同学们在教学楼的中庭聊天,然而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某个在非洲做了多年NGO的同学的故事上;上课讨论,同学们大谈“我在海地地震的时候”、“我在莫桑比克的时候”,而我完全接不上话,无法参与那些讨论,只能结结巴巴地说“在中国……”
我当时很痛苦,觉得自己很卑微,因而不断寻找改变的机会。
“你知道吗?我们国家快把自己卖给你们中国了。”
玛丽索是我的同班同学,她来自厄瓜多尔。一席和她的聊天,点燃了我内心在寻找的某些东西。她跟我讲,在他们国家,有许多中国人,在做很多事情,包括破坏厄瓜多尔最漂亮的一个瀑布。
那个时候,我了解到AC4,一个许多同学都在申请的学校里的学术课题机会,它会资助学生去某个国家做田野调研。于是,我厚着脸皮跑进系主任办公室,向他请教怎么做课题,求他写推荐信;我反复跑AC4的办公室,和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小哥套近乎,打听申请材料怎么写比较容易选中。就这样大概准备了一个月。
一般都说努力会有回报,然而年的寒假前夕,我得知自己到厄瓜多尔调研中国水电项目的方案成功地,落选了。
缺乏有说服力的经历和背景是硬伤。当时我非常沮丧,就像看到许多招聘写着“三年以上工作经验”一样,谁来给还没有经验的人那前三年的经验呢?如果不给机会开始,一个人哪里会有背景呢?
抱怨、沮丧,后来我拿着已经写好的方案,萌生了一个想法:虽然没有申请下来课题,我其实依然可以去啊。
第一个计算是花费,虽然没有人给我报销费用,但是纽约的房租很贵,我把寒假的房子短租出去,纽约飞厄瓜多尔的机票就解决了。而与在纽约过寒假相比,在厄瓜多尔总是便宜的。
第二个考虑是最糟的结果,我是学新闻的,我可以尝试写报道,而哪怕最后什么成果也出不了,当是一次旅行不也不错吗?
寒假前几周,我买了机票,自己到大使馆办了签证,向同学们宣布:我要去厄瓜多尔做调研了,题目是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的环境影响。
厄瓜多尔的海豹
出乎意料地,尽管没有正式的课题与导师,许多老师在看到我认真要去之后,都与我耐心地讨论这个课题的背景、要注意的事项,以及给我介绍他们在那边的人脉;许多同学在知道我要去之后,都会跟我说:“我有个朋友在那边,你可以去见一下。”
加了两个当地朋友的Facebook,知道了一个当地学者的名字,要到了一个环境NGO的名字,我降落在厄瓜多尔首都——基多。
打了个出租车,我首先入住在网上订的青年旅社,在等待几乎一整天之后见到Facebook认识的当地青年尼尔森,在他那里,我了解了许多这个国家的情况,对调研有了基本的思路。
第二天我直接打车到我所知道的环保NGO。在AccionEcologica(环保行动)的总部,我见到了伊斯潘拉兹阿姨。去之前,我非常担心这些人不会见我:我不是学者,也不是有记者证的记者,甚至连个推荐信都没有。然而,我发现自己多虑了。
伊斯潘拉兹告诉我,我是她深度交流的第一个中国人。他们当时在
本文编辑: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://www.jiduoa.com/jdfdl/9337.html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