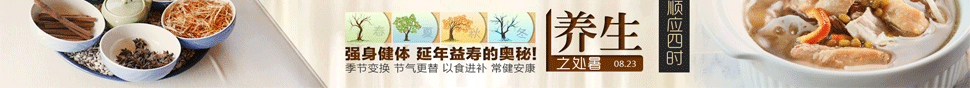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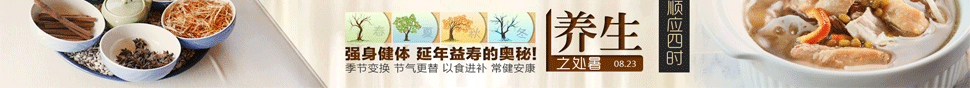
前几天,无意中在新华书店看到由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主编的《筒子楼的故事》一书,里面收录了北大几代教授们对住“筒子楼”那段旧时光的回忆,真实、琐碎而动人。说实话,我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,感觉特别温暖,这本书在一瞬间激活了我的记忆,因为我初来金华教育学院工作时也曾住过近四年的“筒子楼”,于我而言,在那段住筒子楼的旧时光里,确实有温暖,有快乐,更有情感……
上世纪90年代末期,似乎注定我和金华教育学院有缘。因为不能解决正式编制,那年我放弃了留在江西省城一家省报当记者的机会,选择来浙江金华教育学院工作。
我现在还清晰记得,第一天去金华教育学院报道时,作为一位初来金华的异乡人,当学院后勤处处长方顺扬告诉我说——学院安排住宿,那一刻,我内心的喜悦喷涌而出。是的,不用租房,又可以住在校园里面,与书香为伴,与青春学子为伴,着实令我兴奋不已!
那天,我从方顺扬处长那拿到房间钥匙,同时也得知,由于学院住房比较紧张,我和另外一位新来的、叫杨凯锋的音乐教师两人同住一间。当然,我和凯锋老师仅仅同住了半年,第二学期,因为有些老师买了房或成家搬出去住了,学院房间又宽裕了些,所以,后面的几年,我们那些年轻教师都是一人一个单间。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我那时住的那幢楼在学院被称为“3号楼”。那是一栋陈旧而略显“古董”的四层楼(严格来说,只能算三层半,因为最边上一小部分只有三层),当时学院医务室和财务室、后勤处还有1个教室设在一楼;二楼则设有会议室、招待所等;三楼就是我们年轻教师的“宿舍”;四楼全是学生宿舍。
那幢楼我住进去的时候,据说房龄就已超过20年,而且是一幢标准的“筒子楼”。我想,只要稍微上了点年纪、住过筒子楼的人,应该都知道,“筒子楼”的南北都有房间,而作为公共通道的走廊,往往还比较长,颇有一种线条型的延伸感,像极了地铁隧道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们当年住的那幢楼,除去一楼因中间有敞开式大厅光线还可以,而二楼三楼,哪怕是大白天,走廊里如果不开灯,也比较昏暗漆黑,只有东西两头通过窗户能透进一些光亮,咋一进去还真以为是误入了哪个隧道。
我记得当年我一个人住的房间是在“3号楼”的三楼北边靠东,不足20平米,没有阳台,没有阳光,不过,也算是冬凉夏暖,四季分明。那时我们三楼“宿舍区”特别热闹,家家厨房都“设”在外边,都把煤气罐煤气灶摆在自己房间门口边上,油盐酱醋等调料的瓶瓶罐罐就堆放在旁边的旧桌子上。每到吃中饭或晚饭时间,很多老师都不约而同地拧开火,摆上锅,倒进油,炒着菜,刹那间,一阵阵扑鼻的香味,在整个楼道弥漫着。随后,各种菜的香味混合到一起,再夹着老师们的欢声笑语,回荡在长长的走廊里,真是别有一番景致和氛围——亲切、开心、温暖,犹如一个和睦温馨的大家庭。
可以说,前前后后,我在教育学院“筒子楼”住了差不多四年光景,那是一段纯真而又质朴的时光,更是一段充满温暖和快乐的时光。我记得那时除了年龄稍微比我们大些的傅德忠老师,还有短暂住过一段时间的陈文兵老师一家,其他像陈斌跃、周志远、吕凯、徐高虹、应根基、金薇薇、黄山明、周颖华、杨凯锋、吴亚飞、何妮、陈霞、杜祖平、周银水、茅珠芳、邹晓光……清一色都是“70后”年轻老师,年龄相仿的我们,在那个狭小逼仄而拥挤的空间,共同经历着,快乐着、成长着……
陈斌跃,当年同住“筒子楼”的兄弟,中山大学毕业的高材生,或许因为我们俩大学里学得都是哲学专业,平时很聊得来,所以那时经常会在一起吃吃饭喝喝酒,聊聊人生与哲学。可我没想到,他的生命后来竟会因为一场“不成爱便成恨”式的爱情被过早划上了休止符!不知为什么,他出事后,我好些个夜晚一直都失眠,或许是因为他是我要好的朋友,仰或是惋惜他28岁便逝去生命。我记得他出事的第二天,我为他在《金华日报》上写了篇文章《珍爱生命》,到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,我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真实的话“那天,他父亲来学校给他清理遗物时,那场面那情景很是凄凉!当他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抱着他用过的席子、被子、脸盆、书本……一瘸一拐地下楼梯时,我在后面帮他父亲搬电脑,作为大男人的我,那一刻,我竟也泪如花落……”
周志远,当年外语系的老师,一位秋冬季节都很喜欢穿西装的兄弟,身上总是洋溢着一种笔挺儒雅的气质,但实际上志远兄为人大大咧咧,平时也比较擅长“侃大山”。在“筒子楼”,关于他,有两件事“如雷贯耳”,一件就是他大学时代就过了英语专业八级,专业水平一流;还有一件据说他爱人是他大学快毕业那年刚分来的英语老师,这说明他追女孩也是杠杠的!当然,他和他爱人都热情好客,我曾好几次受邀去他房间吃“金华馄饨”,他爱人包的“馄饨”,口味纯正,汤鲜味美。后来,志远兄考上研究生便离开了教育学院,再后来听说他在浙师大当老师了。
吕凯也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位“筒子楼”兄弟,他当年住在正对着楼梯口的那个房间。他和我算是半个老乡,他老家是永康的,但他从小又是随父亲在江西成长读书,当年高考以弋阳县理科第三名的成绩考上北京师范大学。他虽然是心理学教师,但他对哲学比较感兴趣,所以平时有事没事会过来找我谈谈哲学。吕凯兄性格偏内向,好静寡言,为人敦厚老实。或许是太老实的原因,当身边不少年轻男老师都“成双入对”——告别了单身时,二十七、八岁的吕凯兄还是孑然一身,所幸后来他考上华东师大研究生,别离了“筒子楼”,再后来,听说他研究生毕业去了无锡的江南大学任教。
徐高虹,杭州大学教育管理专业出来的才子,呵呵,他当年可是“筒子楼”周末聚餐喝酒的“带头大哥”,我想这可能是缘于高虹兄那非凡的组织能力,特别是他厨艺精湛,烧得一手好菜!记忆中,一到周末,高虹兄住的那个房间就基本成了“酒会沙龙”,想当年筒子楼的那些兄弟们,没去过他“家”吃饭喝酒的恐怕寥寥无几。现在想想,那时候,年轻人经过一周工作的劳累,周末能聚在一起在谁家喝喝酒聊聊天,何尝不是人生一大快事?确实,当年大家在高虹兄家喝酒时,不为别的,只为那单纯的一种快乐,因为在陌生的城市,朋友们相聚一起喝上几杯,足以驱赶生活中的一切烦恼……
还有杭大毕业的计算机老师应根基,那时同事们习惯叫他“阿基”。阿基个子不高但酒量不错,尤其是酒风豪爽。每次“筒子楼”的兄弟们聚在一起喝酒时,他都会喝到脸色苍白、舌头打卷时才舍得放下杯子,然后含含混混地和大家一起“侃大山”。阿基兄后来调金职院去了,算起来我现在已有好些年没见过阿基兄了……
还有那位北师大毕业的美女教师金薇薇,她能歌善舞,多才多艺,我至今都惊叹她作为一位生物老师,却能把印度舞、新疆舞跳出专业水准!她后来凭自己文艺特长,辞职创业,听说在形体及舞蹈培训领域做得“风生水起”,真不愧为名校高材生!
当然,在金华教育学院“筒子楼”一起住过的兄弟姐妹,还有很多很多……。虽然我在“筒子楼”住了差不多四年之后,后来因为贷款买了商品房,便搬离了那曾经熟悉的小房间,而金华教育学院也于年换了新校区,由人民东路搬到了环城北路,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却永远地驻留在了那里,无法搬走,毕竟那里曾有一段属于我的流年岁月。
这个周末,我去了一趟金华教育学院老校区(现金华艺校校区),还特意去当年的“筒子楼”3号楼的楼上楼下转了一遍,显然,现在的“她”已里里外外被装修一新,而且我以前住过的那个房间也已成了别人的办公室。于我而言,那个房间贮藏着那些逝去的光阴,即便现在门扉紧闭,我似乎还是能看见自己当年生活的影子。
站在昔日“筒子楼”的楼道口,望着那笔直似乎正向岁月深处延伸的走廊,那一瞬间,我有些潸然欲泪,是的,那些在“筒子楼”经历过的很多往事,如今都已被岁月沉淀成了一种美好的怀念……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

